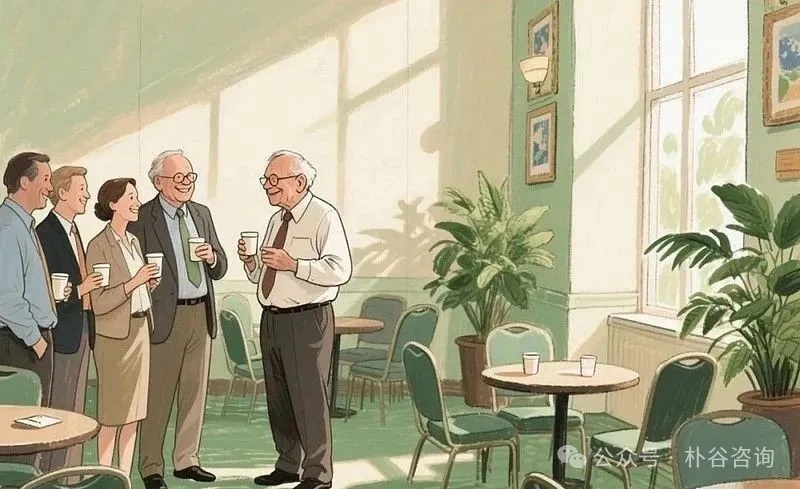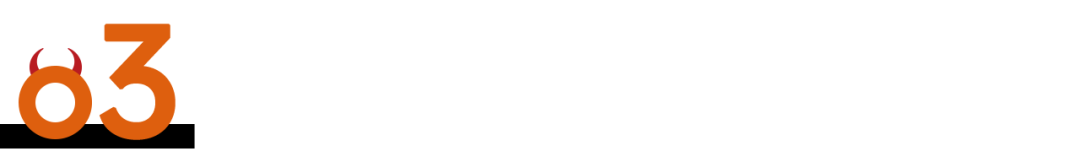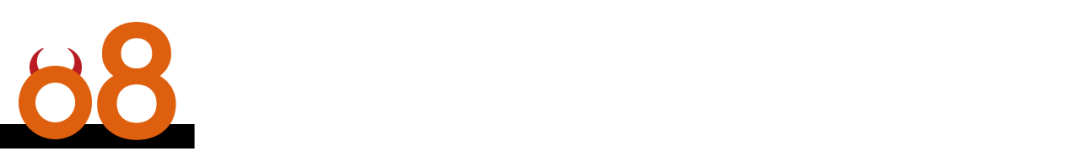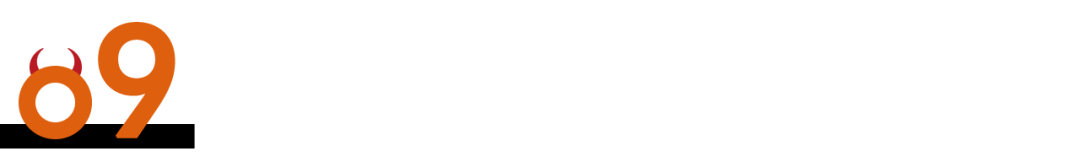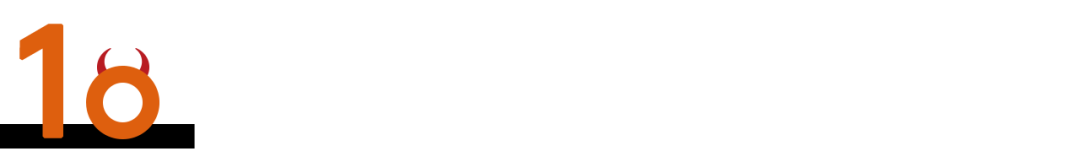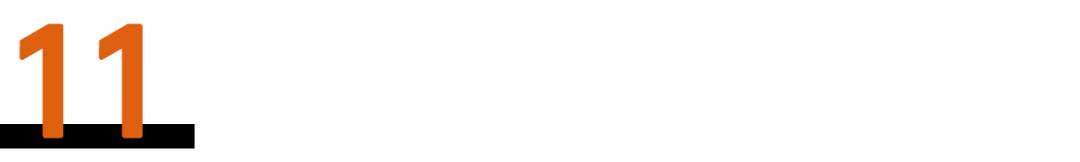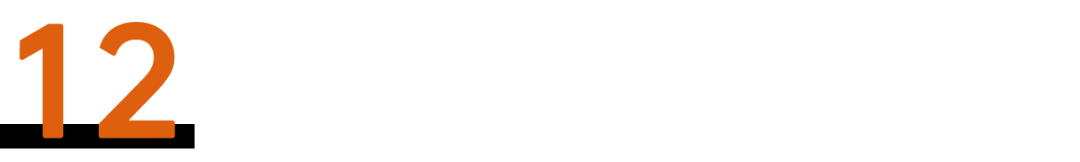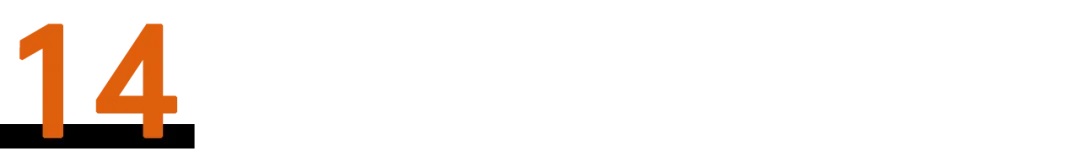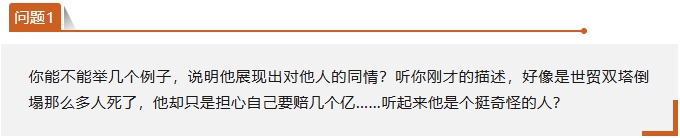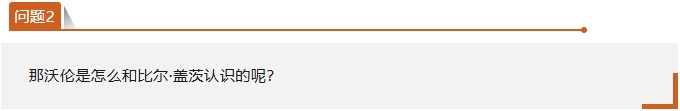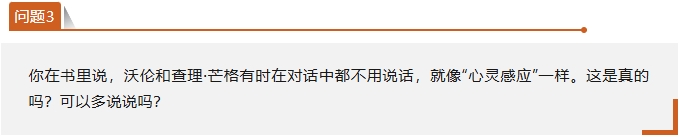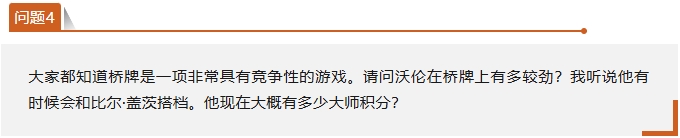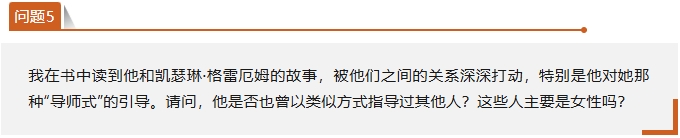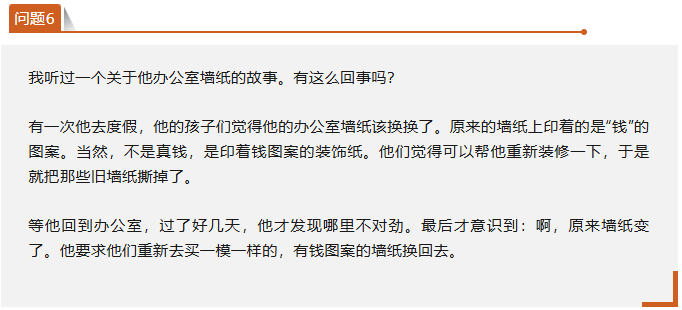那是在1998年。虽然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已经过去了很久,当时他67岁(我就不提自己那时几岁了),而今年他已经要88岁了。
我之所以与他相识,是因为伯克希尔·哈撒韦收购了一家公司——通用再保险(General Re),而我当时是华尔街的一名分析师,正好覆盖这家公司。
(聪投注:在宣布伯克希尔收购通用再保险的新闻稿中,巴菲特列出了促使伯克希尔愿意为这家保险巨头支付溢价的四大“强力协同”因素:
首先,这笔交易消除了困扰通用再保险盈利波动的限制。”
过去,通用再险为了控制盈余波动,不得不放弃某些有吸引力的业务机会,或者大幅缩减已承保的业务规模。这主要源于它作为上市公司,以及希望维持AAA信用评级的压力。考虑到这些背景,通用再险自然无法以可能带来大幅盈余波动的方式来经营。但作为伯克希尔的一部分,这些限制将不复存在,这不仅将提升通用再险的长期盈利能力,也会增强其承保业务的能力。
此外,通用再险还将有更多自由逐步降低对再再保险市场的依赖,从而释放出大量可用于投资的资金。
第二,通用再险拥有拓展其全球再保险业务的巨大潜力。
加入伯克希尔后,通用再险可以根据自身判断,以更灵活的节奏投资国际业务的扩张。
第三,合并将为通用再险带来税务上的灵活性。
在管理保险投资时,若能预期大额应税收入的持续产生,无疑是一个明显优势。大多数保险公司并不具备这种条件。但伯克希尔旗下的保险子公司则不同,它们可以根据伯克希尔多样且稳定的应税收入来源,放心制定投资策略,无需担心未来是否会有足够的应税收入可用。
最后,伯克希尔旗下的保险子公司从不需要担心资本充足问题。
因此,它们在制定资产配置策略时可以完全遵循“最合理的方式”,而不受市场剧烈波动对资本影响的束缚。事实上,这种灵活性在过去曾多次为伯克希尔旗下的保险业务带来巨大优势。)
所以我决定借此机会研究伯克希尔,因为保险业是它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正是研究这个领域的专家。
但我知道,巴菲特肯定不会接受我的采访。因为他出了名地不喜欢华尔街,他几乎从不接受采访,也不与华尔街打交道。
他说过的话,比如,“如果你想保住你的操守,走过华尔街时得捏着鼻子”,就是一种相当不屑的态度。
所以我开始了这个项目,完全没指望能像其他分析师那样,去找管理层问问题、核对资料。但后来他好像得知了我在做这件事,可能是有人告诉了他。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我的助理走进来说:“你有条沃伦·巴菲特的留言。”然后递给我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要我回拨。
我当时简直吓得发抖,根本无法想象要亲自给沃伦·巴菲特打电话,但我知道我得马上回应。
于是我拨通了那个号码,电话那头一个声音说:“Yello~”
我说:“您好,我是爱丽丝·施罗德,我打电话找巴菲特先生。”
他答道:“哦,爱丽丝!谢谢你回我电话。”
就在那一瞬间,我才意识到,电话那头就是他本人。他居然亲自接电话,还把私人号码给了我。
这真是太震惊了,在他那个层级的人,根本不该把私人电话随便给别人。
后来我才知道,他做事很谨慎,会事先调查,而且只会把这条私人号码给他确信不会随意外传的人。因为他真的会亲自接电话。而他确实调查过我,但当时我一无所知,只是惊讶得不知所措。
在那通电话里,他对我说,我主动在做这件事,却没有向他提出任何请求,他很喜欢这种做事方式。他喜欢那些不来求他办事的人。
他说他读过我写的研究报告,喜欢我的思考方式,也喜欢我的写作风格。所以他愿意配合我,还说他愿意让我成为唯一一个他愿意合作的分析师,可以和他直接对话。
他邀请我去奥马哈,花时间参观他的企业,只要我需要,他都可以接受采访。
接着他说,几周后他会来纽约,到时候我可以和他、还有他妻子苏珊(Susie)一起乘坐他的私人飞机返回奥马哈,在飞机上继续采访他。他还会亲自带我参观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公司业务。
那通电话和这次机会,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沃伦·巴菲特是什么样的人。
说实话,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坐私人飞机,所以我非常紧张,甚至不知道自己该怎么举止才合适。
我那天早上在酒店见到他和苏珊,然后我们一起前往机场,登上那架湾流G4——当时是全球最大的私人飞机之一。
我被飞机的美丽所震撼。我们坐下来,他在一张桌子对面和我面对面。空乘人员走过来问我们早餐要吃什么:“我们可以做煎蛋卷、松饼、华夫饼,或者班尼迪克蛋……”开始列出一长串菜单。
我心想,哇,好想来一份煎蛋卷啊。但沃伦说:“我要一包薯片和一罐樱桃可乐。”我也说:“那我也一样。”
接下来的四个小时,我们飞往奥马哈的途中,沃伦一边讲话,一边不停地吃薯片,我也就跟着他一起吃。
这其实是我人生中即将开启的10年旅程的一个预兆。在那之后,我会和沃伦·巴菲特共进无数顿饭,也因此体重一路飙升(笑)。
我当时紧张得不得了,完全不知道该问什么,嘴都快结巴了,提的问题也都非常愚蠢。事后回想起来,在我后来真正了解他之后,我都不敢相信自己当时的表现有多糟糕。
但他其实已经习惯和紧张拘谨的人打交道了,所以他很自然地引导我,帮助我放松,我们还是聊得很顺。
不过那次最特别的部分,是我们到达奥马哈之后发生的事。
他先带我去了他的办公室。那间办公室当时的装潢风格,用现在的话讲,跟美国的车管所差不多,甚至有点像我想象中的监狱(笑)。
那种非常脏兮兮的墨绿色墙壁,地毯看起来大概有二十多年没换过,也没清洁过。但他对这些完全无所谓,根本不在意。
我们在那里待了几分钟后,他带我去了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这是他收购的一家公司,当时是北美最大的家具商场,占地数十英亩,可能超过一百英亩。
沃伦亲自带我参观。他比我高大约六英寸,腿应该比我长八英寸。所以他迈开步子走路,我只能在后面小跑着追。他就这样带着我穿越了这片浩瀚如迷宫般的商场。
一路上他指着不同的区域对我说:“这边是祖母钟专区,这个款我们一年能卖48台。”接着我们走到床垫区,他又说:“这是我们卖得最好的一款床垫,我们每平方英寸能赚两美元的利润。”
我开始感受到他掌握的细节有多么惊人。
最后他说:“我们去地毯仓库看看吧。”
这家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是他从一个名叫罗斯·布鲁姆金(Rose Blumkin,著名的B夫人)的女人手中买下来的。
她是一位只有不到1米5的、身材娇小的犹太裔移民,曾经穿越西伯利亚,在动荡的东欧“屠犹暴乱”中逃出生天,历经两千多英里的旅程来到美国。
巴菲特收购家居商场时,她已经非常高龄了。
地毯仓库,是罗斯·布鲁姆金最在意的地方,可能因为她小时候睡在光秃秃的木地板上,只铺了一层稻草,所以地毯对她而言格外重要。
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每年销售上百万码的地毯,仓库也非常大,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地毯。
我们走进地毯仓库,沃伦照例走在前头,我继续在后面小跑跟着。他一边走一边说:
“那边那个棕色的,是我们卖得最好的款式。我们每周能卖出2000码,利润率大约是22%。不过这周我们打了折,只能赚11%左右。”
“这边这个地毯,销量没那么高,但我们从来不用打折。所以虽然这周可能只能卖1500码,但我们仍然能拿到20%的利润。”
“角落那一堆,看见了吗?这些是罗斯留下来的,她以前不愿意把任何产品的售价压到低于进货成本。但我说服了她,把库存清掉才是更明智的选择。所以这些我们每卖出一批,要亏掉20%。”
“这个绿色的,是我们卖得最差的款。我们只能用进价的一半把它处理掉。”
然后我们继续在地毯仓库里走,穿过一排又一排、一列又一列,他向我详细解释每一种地毯的摆放位置、款式、成本价、售价、每周销量和利润率。
正是那一刻,我开始意识到,他绝非一个普通人。毕竟,这仅仅是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众多公司中的一家。
之前在他办公室时,他还给我看了喜诗糖果(See’s Candies)的一些报告。那是一家伯克希尔旗下的巧克力连锁品牌。
我当时有些吃惊,因为那份报表详细列出了全国一百多家门店每一周的销售数据。
他解释说,为什么那一周圣塔莫尼卡店的销量要优于萨克拉门托店。
而他对信息的敏锐掌握,在伯克希尔旗下四十多家公司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就像一块海绵,能把所有细节全盘吸收、彻底消化。那一刻我开始明白——这正是他成功的关键所在。
我回到纽约后,写了一篇分析报告,引起了不小轰动。因为在那之前,从没有人真正写过一篇详尽的伯克希尔研究报告。
接下来五年间,我每年大概见他两次,一次是参加股东大会,另一次是他每年举办的派对。他也常邀请我去奥马哈见面。
他总是说:“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但我从没真打过去过。我总觉得他肯定很忙,而我实在是最没有资格去占用他时间的人。
但他却经常主动打电话给我,我们会聊一些事情。时间久了,他变成了我最想听取意见的人。如果有什么重要事件发生,我会破例给他打电话,因为他的看法是我最想知道的。
五年后,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2001年9月11日。
那天我在纽约,亲眼看到第二座大楼被撞。我有很多朋友都在那两座楼里——这对很多人来说,当然都是极其糟糕的一天,留下了很多难以面对的回忆。
但在那之后的第二天,我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沃伦。
我只是想听听他对这一切的想法。
令我意外的是,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愤怒——这完全不是我预期的反应。
那是我见过他为数不多、真正非常愤怒的两次情形之一。
他当然已经消化了“9·11”带来的震撼,也在很快之后开始深入思考这件事。我们后来确实围绕恐怖主义与风险进行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探讨。但让他愤怒的,其实并不是袭击本身,而是另有原因。
就在六个月前,他曾亲自找过伯克希尔旗下两家保险公司的负责人谈话。
一家是国家赔偿公司(National Indemnity),由阿吉特·贾恩(Ajit Jain)负责,你可能听说过他,后来成为伯克希尔董事会成员;另一家是通用再保险公司,这家公司正是我当年在华尔街分析、从而引起我关注伯克希尔的那家公司。
他当时要求这两位负责人去查清楚:公司在世贸中心的保险敞口到底有多大?有多少客户在那里?如果这两栋楼真的出了事,伯克希尔需要赔多少钱?
等他们整理好数据回来后,他对他们说——7月是商用保险续约的常规时间点,我要求你们尽可能取消或不再续保这些保单。
两人中,阿吉特·贾恩照办了,大幅削减了国家赔偿公司在世贸中心的风险敞口;但通用再保险那边的人却没有听从指示,完全忽视了他的要求。
结果,伯克希尔为此承担了 24 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沃伦非常愤怒。
他把这称为一次“非受迫性失误”(unforced error),就像棒球术语中说的那样,这是一次本可避免的错误。他事先已经预见了风险,也做出了明确决策,但这些却被无视,最终导致巨额损失。
而且对他来说,那不仅是公司的损失,更是他自己的钱,因为他是伯克希尔的最大股东。
这个故事让我震惊,不只是因为他当时有多愤怒,毕竟我只见过他两次这种愤怒的状态,而且这两次都是:他发出明确指示却被忽视,最终损失了钱。
那种愤怒,是一种冷峻的怒火。
但更让我震惊的是,在“9·11”发生前六个月,他就已经做了这些判断和安排。
当然,他本人也会第一时间澄清:他并没有预测“9·11”,完全不是那样。但他知道的是:恐怖袭击不是没有发生过,世贸中心这类建筑存在大量集中风险,而且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个安全的地方。
他拥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思考方式,能把抽象的系统性风险预判转化为具体决策,这让我极为震撼。
2003年6月,我飞去奥马哈,在当地的达布尔特里酒店安顿下来,开始和沃伦的合作。
那时,他们正开始翻新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早就是一个角落办公室,这次也重新装修了。换上了棕色地毯、棕色木质家具,配棕色布艺靠垫,墙壁贴了棕色壁纸,角落窗户装了棕色木百叶帘——这些百叶帘他永远拉着,不让天光进来,因为他说不想被窗外的天空分心。
所以他的办公室给人的感觉,有点像……关在一个布谷鸟钟里。
接下来的整整一年半,我几乎都在这个布谷鸟钟里度过,确实有点压抑。
为了逃脱,我经常溜进档案室。注意,是档案室们(rooms,复数)。
如果你曾看过他在电视上办公室导览的纪录片,你可能注意到:他从不带人去档案室。
他总是说自己“没有保存所有东西”,但我觉得他的“所有”这个词,定义相当宽松。
他确实有两个巨大的档案室,保存了自己每一笔投资的资料、每一家研究过的公司的资料。
还有一整面半隐藏的文件墙——专门是关于人物的档案。当然,它们并不是像胡佛(J. Edgar Hoover)那种骇人听闻的秘密档案,但我第一天在那里,就发现了关于我自己的资料夹。
他喜欢写信,所以与每个人的往来信件也都被整理归档。这个习惯非常有逻辑。
不过,他对我能否查阅这些资料,其实是非常紧张的。他唯一对我设限的,是:不能发表任何他写过、说过、会让他人难堪的话。
他说:“你想写什么关于我批评自己的话都可以,我不在意。但如果是我说过谁的坏话,请不要写进书里。”
我回答:“嗯,这得看具体内容。”确实后来有一件事,我决定不写出名字,之后我会讲那个故事。
(聪投注:在巴菲特宣布退休后,《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采访了爱丽丝·施罗德,这段访谈在2025年7月29日发布。施罗德分享了这位“奥马哈先知”在处理称赞与批评方面的方式。她说:
“他曾用不同的方式对我讲过同一件事:当你跟某个人讲话时,就算你说了99句夸奖,只夹杂了一句很轻微的批评——他们记住的只会是那句批评。这就是他对待员工管理的方式。
起初我并不完全理解,但在与他长时间相处后,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现实中也是如此,一次次印证。如果你真希望别人感受到你的赞赏,那就必须是毫不掺杂的、纯粹的称赞。”)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我坐到他办公室的沙发上,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最核心的问题:“沃伦,如果你必须深入思考、坦诚回答:你成功的真正秘密是什么?”
他立刻回答了两个字:“专注。”
但他口中的“专注”,并不是你我理解的那种专注。
他所说的“专注”,远不止是他在地毯仓库里记得那块二十年前的绿色长毛地毯得清仓处理。
我后来慢慢理解到:如果沃伦·巴菲特买下了一家比萨店,他不会只是看财务报表,然后问几个相关问题。
他会从最基础的原料开始研究,比如小麦的历史价格走势。他会算出做一张披萨需要用多少水,这些水的成本是多少;他会搞清楚披萨酱的配方和价格,深入研究奶酪和其他配料的成本,甚至思考是否能用更少的原料而不影响口感。
他还会研究各种型号的披萨炉——包括它们的购买成本、运作效率、维修费用,以及使用寿命。他会去了解这家披萨店的方方面面:员工和外卖员的薪资水平、流动率、可靠性;店铺的租赁条款是否合理。
总之,他对一家披萨店的了解,会从“小麦的价格”开始,一直延伸到运营链条上的每一个细节。
这就是我所说的专注。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专注力。而随着我慢慢了解他,我也见识到了他个人生活中的那种专注。
我很早就认识了阿斯特丽德(Astrid),她现在是阿斯特丽德·巴菲特,是他的第二任妻子。
当时他们住在奥马哈,而沃伦还和他的第一任妻子苏珊保持婚姻关系,苏珊住在旧金山,他们已经各过各的生活。
我后来也在旧金山见过苏珊。但阿斯特丽德是我非常重要的线索来源,她告诉了我一些故事,那些故事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沃伦的性格,比如这个:
你可能听说过,沃伦喜欢打桥牌,而且是每周三晚,通常就在他们家里的家庭活动室。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房间,差不多有这个舞台那么长、两倍那么宽。装修风格看起来像是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很可能就是那时候装的。
其中一面墙是长长的窗户和窗帘,还有一台电视。阿斯特丽德会坐在那里看电视。另一面墙上是房门。而在这边是沃伦的电脑桌,上面放着他的大显示器,他就在这里打桥牌。
有一晚,一只蝙蝠飞进了房子。蝙蝠在房间里乱撞,撞到墙壁,缠到窗帘上,发出各种响动,场面很混乱。阿斯特丽德吓坏了,开始大喊:“沃伦,帮我!这儿有蝙蝠,快帮我!”
但沃伦连头都没转一下,手也没离开鼠标,只说了一句:“它又没打扰我。”
阿斯特丽德只好自己打电话叫了捕捉服务的人。那人过来,把蝙蝠处理掉,整个过程花了大概一小时。而这整整一小时里,沃伦全程打桥牌,眼睛一次都没离开过屏幕。
这就是另一种专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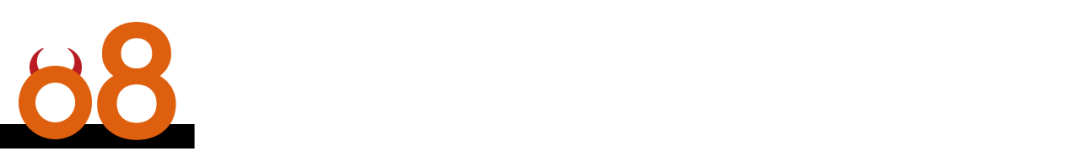
我们渐渐开始有了一些私人层面的了解。
他做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开始温和地引导我走出当时的婚姻。
他认为,我的丈夫并不适合我。但他的方式极其细腻,不会直接劝你离婚,而是用问题引导你思考。比如他会问:“如果你像他那样对待你自己,你会接受吗?”
我一听就明白了:当然不能。但在那之前,我从未以这种角度去看待自己的处境。就这样,他像滴水穿石一样,一点一点让我意识到,也许我真的该离婚了。
当然,公允的讲,我的父亲和家人当时也劝过我,所以并不完全是沃伦一个人的影响。但他确实表现出一种想要介入的意愿,一种近乎父亲般的态度。他始终觉得,我当初嫁错了人。
后来我再婚时,他不光说要“把把关”,还真的“通过”了我先生。他非常喜欢我的第二任丈夫,送了我们一份特别棒的结婚礼物,还亲自录了一段祝福视频。他认为这一次我选对了人。
他说,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去选择对的人。说实话,他说得没错。
那时候我决定,在离婚的过程中买套房。我告诉了他——
那段时间我生活里发生了很多事,一切显得有些混乱。所以我就自己去看房、出价、签了合同。
平常我们跟沃伦聊天,多半是围着他说,很少聊我自己的事。所以当我跟他说我买了房子时,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吗?”
我说:“嗯……我已经交了定金,也签了合同。从技术上讲,是可以违约退出的,但那样就得损失定金。”
那是2004年。
他的反应是:“房地产市场要崩了……不过,如果你能撑满10年,到时候起码还能以原价卖出去。”
后来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他说自己并没有预见到房地产危机,我相信他确实没料到,危机会这么严重。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2004年,他就已经看出房地产市场有泡沫,只是没想到泡沫会破得那么惨。
不过我得告诉大家:我真的在10年后把那套房子差不多以原价卖掉了。而这10年里的日子,确实很不好熬。
所以他说得没错,甚至让我有点发毛,让我又想起“9·11”前他做的判断。
他这种“知道一些别人没看到的事”的能力,虽然我从来没觉得他有什么超自然力量,但当他公开预测一件事,或表达某种担忧时,我现在都会把它当成“福音”来看。
我听过很多人质疑,说他有意说这些话,是出于某种目的。但我不这么想。我和他共处那么长时间之后,我的看法是:他只是非常擅长把信息连接起来。
有趣的是,这次他对房地产的判断,其实来源于一个他完全没兴趣的领域。
他自1956年起就住在同一栋房子里,而且就像我说过的,看起来可能从1976年之后就没再装修过。
他不投资房地产,也不买任何不动产类资产,这是他有意回避的一整个领域。
有一次我甚至问他,他卧室的墙是什么颜色,他回答说:“不知道。”我还真相信他不知道。考虑到他办公室一片棕色,我甚至怀疑他知不知道自己整天坐在棕色的世界里。
不过你可以看出,他确实在影响我。
而我那时正是他的传记作者,按理说我的职责是保持客观。
但我也看得很清楚:当你在写一本关于一个活着的人的书时,你多少会被这个人所吸引。
而我当时已经被他整个家族所吸引了。
所以,正如你所看到的,沃伦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他会深刻地影响身边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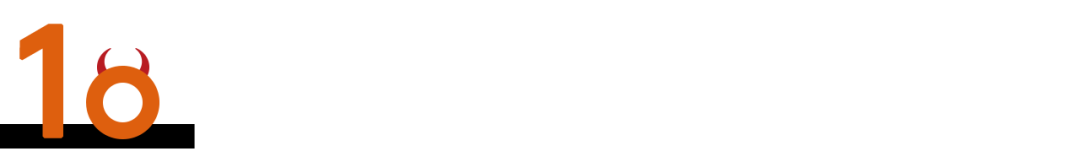
而他影响力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或许就是他和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以及《华盛顿邮报》的故事。
这是另一种类型的专注。
他在《华邮》股价低迷、公司面临困境时买入了股票,但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投资机会。他看到的是:这家公司由凯瑟琳继承,而她是在丈夫自杀后被迫接管公司。她没有商业经验,尽管自身也算得上是一位有能量的女性,但她个人其实非常没有安全感。
沃伦意识到,通过和她建立友谊,他不仅能影响她,也能提升这笔投资的成功概率。
而与此同时,她也让沃伦的生活更加丰富。
我在采访她儿子唐·格雷厄姆时,凯瑟琳已经去世了。唐带我去看了一批资料,那是沃伦多年来寄给他和他母亲的“商业教学包”——这简直是份令人惊叹的礼物!
凯瑟琳和沃伦当年经常一起社交。她长期住在华盛顿,经常把他介绍给各种富人、名人、政界人物,帮他打开政治圈与上流社会的大门。
但沃伦给她的回报,却鲜有人知。
他每天会亲自准备一份资料包:里面包括报纸剪辑、简报、信件、行业通讯——他自己读过、划过重点、在边角写上批注,是他亲自挑选并整理的“商学院教材”。目的很明确:教他们怎么经营一家好公司,怎么理解宏观经济,怎么投资。
这件事,一做就是好几年、好多年。
唐允许我复制了其中大部分内容,所以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份。这是我自己私人的“沃伦·巴菲特大师课”,虽然是他送给凯瑟琳和唐的,但我算是间接受益者。
他说自己只会做一次这样的事,绝不会再做第二遍,因为那实在太花时间、太费精力了。
这段影响的结果是,沃伦后来加入了《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
有人甚至说他才是《华盛顿邮报》的“影子CEO”。我不认为那是真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这家公司的决策、发展历程和未来方向,确实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这一笔投资,后来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历史上最成功的投资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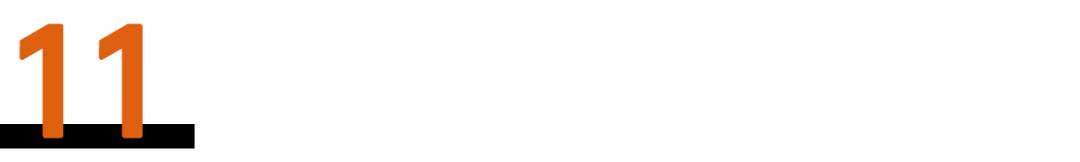
再举一个例子,GEICO(盖可保险)。这同样体现了他的专注,而且是那种极端持续的专注。
他第一次听说GEICO,是在青少年时期,在图书馆里读到它的资料。他当时特地从奥马哈跑到华盛顿(GEICO总部所在地),是在一个下雪的星期六早晨。
他进了公司大楼,碰巧遇到公司总裁洛瑞默·戴维森(Lorimer Davidson)在上班。于是他走进去,和他聊了四个小时,纯粹为了学习,想了解汽车保险行业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之后他就回去买了GEICO的股票,把自己所有的钱中75%都投进去。他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最看好的证券》(The Security I Like Best),发表在《商业与金融纪事》(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上,那本杂志在当时就像是现在的《巴伦周刊》。
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持有GEICO股票。
不过,真正让他获得控股权,是在20年之后。那时他终于有了足够多的资金,而 GEICO正好陷入麻烦、估值低廉,他就出手买下了公司很大一部分股权,相当于获得控制权。
那是1976年的事。
而在这20年间,他始终和洛瑞默·戴维森保持联系。
他认识了GEICO的其他管理者,也定期去公司拜访,深入了解他们的业务运作。他想拥有GEICO,他渴望GEICO。最终在1996年,他买下了这家公司剩余的全部股份,彻底将其收入囊中。
换句话说,他整整追踪了这家公司40年。他对它了如指掌,了解得越多,就越想把它真正变成自己的。
如今,GEICO已经是美国第二大汽车保险公司,可能也是最赚钱的一家。但在他买下的时候,它的行业地位大概还排在第20名,和像美国安泰(Allstate)这样的巨头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几乎不被视为重要的竞争对手。
但沃伦在很早的时候就看到了GEICO的潜力,并用40年时间慢慢实现了“收购”这个目标。而1996年并不是终点。再往前推22年,到现在,这家公司又经历了巨大成长。这个故事在我看来,真是不可思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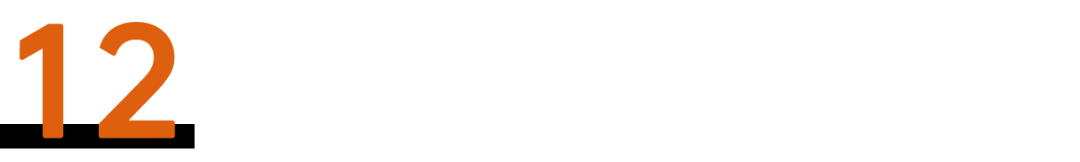
不过,正因为他对商业的关注如此专注,也会带来某种“视野盲区”。
我和沃伦越来越熟之后,也注意到他有些事情看不到。如果你对某件事专注到一定程度,你真的会对眼前的一些东西视而不见。
那时,我已经写了两三年书,前后有一年半时间,不是在奥马哈,就是在和他一同出行的路上。之后我也多次去奥马哈,可能一共和他见了上百次面,一次次的长时间相处。
有一天,我决定跟他开个玩笑。我在康涅狄格州的家里打电话给他,说:“沃伦,你知道我头发是什么颜色吗?”
我在电话里放起了《危险边缘》(Jeopardy)的配乐,一边等他的回答。
然后,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长的沉默,最后他终于开口说:“不是黑色。”
这回答相当精确,他给出了他所掌握的全部信息(笑)。
到了2006、2007、2008年,我们开始讨论一些很深入的话题,比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
这时我直接问他:“你觉得,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他回答我:“人生的目的,是让那些你希望爱你的人,真的爱你。”
我花了一点时间去咀嚼这句话。大多数人可能会说:“人生的意义是被尽可能多的人爱。”但他不是这么说的——他关注的是“你希望谁爱你”,而你希望的是“命中率100%”。
如果你只希望三个人爱你,那你就希望那三个人都爱你;如果是50个人,那你也想全中。但你不一定想要1000个人爱你。
我后来越来越明白,沃伦其实非常渴望被爱。你如果读过《滚雪球》,就会知道他小时候几乎没被好好爱过。长大之后,他学会了去渴求那种爱,并努力在他人那里去寻找。
他曾跟我讲过关于“被爱”的重要性,也讲过名人世界的孤独。
如果你既富有又出名,尤其是同时拥有这两者,那么真正获得“被爱”是很难的。
因为很多人,即便自己没意识到,也往往是带着目的接近你。他们有自己的小算盘。你会被搞得很混乱,分不清谁是真朋友,谁只是冲着你的位置或财富来的。
结果就是,你会被邀请去各种聚会、白宫晚宴,甚至去奥古斯塔打高尔夫。但那并不等于你被真正地爱着。
你会被邀请上各种榜单,什么“最具影响力40人”、“十大商业领袖”之类,也会上杂志封面,看上去风光无限。但这其实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

沃伦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只要我还活着,我不会告诉你这个故事讲的是谁。但如果哪天我再发表这个演讲,而他不在了,你又恰好在场,我会告诉你。但不是现在。”
他说,有一个人,自以为被所有人爱戴,其实他身边没有一个人真心喜欢他,大家都受不了他,而他自己完全不知道。
如果有一天他在台上演讲时突然心脏病发作跌进观众席,居然不会有任何人打911:不是他的妻子,不是他的孩子,也不是他的同事或所谓的朋友。所有人都会冷眼旁观,不会出手相救。
沃伦说:“我永远不想变成那样的人。我想成为一个真正被人爱的人。”
我能看出来,他是真的在意这个。
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多年写作过程中,我接触了不少跟他打过交道的生意伙伴,他们当中不少人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我逐渐意识到,沃伦·巴菲特希望被爱的人群,并不包括所有做生意的对象。有时候,对他来说,钱更重要。
我采访过一些对他心存不满的人。他们觉得在某笔交易中吃了亏,被他压价甚至收割了。他确实对一些交易提出了非常强硬、甚至可以说是冷酷无情的条件,在《滚雪球》里你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故事。
但神奇的是,即使在多年之后,那些人对他还是充满好感。
他们会说,“我真是太生他气了,当年他在某某交易中那样对我……但我还是喜欢这个人,没办法,他就是让人喜欢。”
其中一位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罗斯,她是内布拉斯加家具城的创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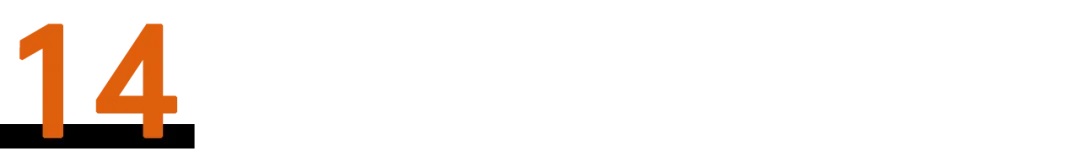
我第一次去那里采访她时,还记得自己穿越她那巨大的地毯仓库跑步的情景。
罗斯在90多岁的时候把公司卖给了沃伦,但95岁那年,她因为不满孙子们经营地毯部门的方式,愤然退出,并在街对面买下一处仓库,亲自创办了一家对标的新家具公司。
一年内,她的新店按面积计算的销售额就已经碾压了原先的家具城。
当地的《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当然对此大肆报道。毕竟两家隔街对峙、还都是一家人斗气,这种故事再吸睛不过了。更别提对方是一位96岁的老太太。
两年多以后,沃伦终于举白旗认输。他不仅在生意上落于下风,更重要的是,这场家族内战引发了对原家具城的巨大负面舆论。
而他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是,罗斯其实一直对他耿耿于怀。因为她后来觉得,当初把公司卖给他的时候,价格压得太低了,自己吃了亏。
她的家族成员可能不会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个,但他们私下里告诉我,罗斯确实非常生气,她认为自己“至少少拿了3000万美元”。
在1980年代,这可是一大笔天文数字。
那笔钱放在今天依然是一大笔财富,而在当时更是惊人。罗斯后来觉得自己有点被利用了,因为当初在把公司卖给沃伦时,还有一位竞争对手也在出价,对方愿意出更高的价格。
但她拒绝了那个对手,只因为他们是德国人。于是她选择了把公司卖给沃伦。
所以这其中确实有一些情绪因素。但即便如此,她依然像其他人一样,深爱着沃伦。
经过两年多的竞争僵局后,沃伦买了一束二十多枝粉色玫瑰,亲自登门拜访。
罗斯只在家具店环境中才觉得自在,所以她的女儿们特地把家里布置成像家具卖场一样,连家具上的价签都没摘掉。
于是沃伦就坐在一张还挂着价签的沙发上,旁边的台灯上也挂着价签。他把花递给她,开始一番恭维,说:“没有你我真的干不下去了。我需要你回来。请让我出500万美元,把你的新公司买下来,我们一起回归。”
但这笔交易有个“附加条件”:当时罗斯已经98岁了,而沃伦让她签了一份竞业禁止协议。
不仅如此,这份竞业协议的期限是五年,而且是“从她辞职之后才开始算起”。
也就是说,如果她第二天就离开,那竞业协议将持续到她103岁;如果她干到100岁才离开,那协议就会约束她到105岁,甚至更久。
(聪投注:B夫人出生于1893年12月3日,于1998年8月9日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去世,享年104岁,所以基本上,她恰恰好活到了竞业协议失效。
巴菲特为什么没有在1983年第一次要求签订竞业禁止协议呢?他的回答是,“我当时还年轻,缺乏经验。”嗯,那时的巴菲特53岁。)
我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我在伯克希尔的档案室里无意中翻到这份协议,之前从未有任何媒体披露过这个故事。
我看到协议上,她是用“X”签的字,因为她从未学会阅读或书写英文——但她心算能力非常惊人。不过英文,她确实始终没能掌握。
我把这份协议拿去问沃伦:“你为什么觉得一个98岁的老太太需要签一个5年期的竞业协议?”
他回答说:“因为我真觉得她可能会干到永远。”
“而对于罗斯,我觉得我需要一份‘比永远还多五年’的保障。”
更有趣的是,罗斯·布鲁姆金是唯一一个能让沃伦·巴菲特产生竞争心态的人。
因为他也想永远经营伯克希尔·哈撒韦。
如果10年后你去找98岁的沃伦·巴菲特,递给他一份竞业协议,说让他签一个“工作到103岁”的协议,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签下。他巴不得!
如果能再活五年、再多干五年——那比什么都让他开心。
不过,假设今晚站在台上的不是我,而是他;假设他不小心从台上跌落、突发心脏病……
我想,那一刻对他来说,反而可能是人生中最满足的时刻。
因为他会听到台下数百人一起拿起手机,拨打911……他会知道,自己被真正爱他的人所爱着。那其中,也包括你们所有人。
而这,甚至比“再活五年”更美好。
谢谢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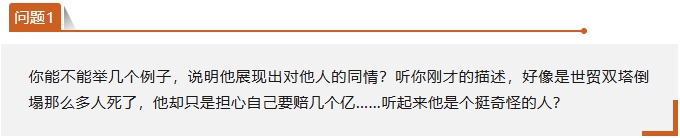
施罗德 他确实是非常“左脑型”的人,讲究逻辑和分析,这是肯定的。但我确实看到他表现出同情的一面,尤其是对他熟悉的人,他的感受会更深。
比如在奥巴马医保出台之前,也就是2000年代那会儿,他对自己身边一些人——包括伯克希尔的员工、退休员工,还有他认识的一些朋友——很担心。他担心他们会因为得了重病而被医疗费用拖垮。
他为此设立了一个专项基金,拿出2000万美元,挑选了一些具体的人,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哪天遇到严重的健康问题,医保不够用,我来补,确保你们可以安心接受治疗,不会破产。
这是那个年代很多人面临的真实困境,而他愿意主动去解决。
还有就是,如果他觉得合适,他愿意出面担保别人的声誉。他会打电话、帮忙牵线、让朋友拿到应得的资源。
他做过很多非常贴心、周到、体面、为别人考虑的事。
我再讲一个很短的故事。
他年轻时和一个叫范妮塔·马·布朗(Venita Ma Brown)的女性约会过。她当年是“内布拉斯加州小姐”,非常漂亮,后来嫁给了他朋友。但她的精神状况可能一直不太稳定。
她离婚之后开始给沃伦写信,一写就是几十页,全是诅咒、指责,说他有多可怕、多糟糕……然后半年后,又写来一封很平静的信:“亲爱的沃伦,我很想你,你最近怎么样?”
你想,换作99%的人早就拉黑她了,对吧?可沃伦没有。
他决定:她要是发疯的那种信,我就不理;但她写来那种正常人格的信,我就认真回信,语气体贴、内容温暖。就这么来来回回写了好多年。
我家里有他们通信的整套档案。
令人惊讶的是:她后来真的变好了。精神状态慢慢恢复,后来还回去参加高中聚会,跟沃伦的朋友们见面,一切都很正常。
我相信,沃伦就像驯兽师一样,用极大的耐心和温和的方式,一点点“消解”了她那些情绪失控的行为。他愿意花时间做这件事,要知道,他是那种把时间看得极其宝贵的人。但他依然选择付出,只因为他觉得这是对的事。
如果你现在给我两个小时,我还能说出五十个这样的例子。所以,是的,他真的非常有同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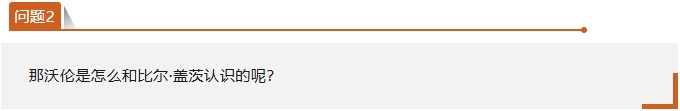
施罗德 是凯瑟琳·格雷厄姆牵线让沃伦认识了比尔·盖茨。
当时,比尔和梅琳达可能还没正式交往,或者刚开始约会,还没结婚。
凯瑟琳有个密友,在华盛顿州的班布里奇岛有一处宅子,那年他们去那里过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
那位朋友刚好认识比尔的母亲。盖茨太太是西雅图极具影响力的社交名流,后来去世了。她家在胡德运河有一处住所,盖茨家正好在那里办派对,希望能见见沃伦;凯瑟琳也希望沃伦能和比尔见上一面。
可问题是,沃伦和比尔都不想见对方。比尔说:“我为什么要见一个来自奥马哈的老投资人?”沃伦也说:“我对科技一点也不感兴趣,我干嘛要见这个电脑男孩?”
他们最后还是去了。比尔说:“我最多跟他聊10分钟。”沃伦也说:“我最多跟他聊10分钟,然后咱们走人。”
他们见面后,沃伦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能不能告诉我,IBM是不是个值得投资的公司?我该不该买?”
然后比尔就开始说了。
比尔其实不是那种社交非常自然的人,但只要你问到他熟悉的领域,他的表达就会非常精彩。
可以说,沃伦问了一个入门级神提问。
结果就是,这10分钟变成了几个小时。他们两个几乎形影不离,书里有一张他们在水上飞机旁的海滩上散步的照片。后来大家几乎是去“把他们俩从对话中拽出来”,才让他们注意到还有别的客人在派对上。
之后的故事就顺理成章发展了。
沃伦教比尔投资的理念,比尔教沃伦理解科技行业。
虽然沃伦一直没怎么买科技股,因为他认为科技行业很难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公司生命周期都很短。但他后来在股东大会上承认,他错了,他低估了Facebook、Google和Amazon的网络效应,没想到它们竟然能如此长期维持优势并持续盈利。
他说,“我们当初本来可以理解这一切,我们完全有能力搞明白,但我们没去做,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在熟悉的领域里做得也挺好。”他称这是自己最大的失误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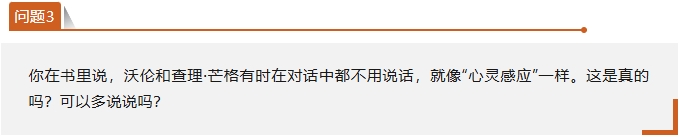
施罗德 当然。早年的时候,沃伦和查理几乎是24小时形影不离,一聊就是十几个小时。
他们现在已经熟悉到一个程度:在任何情境下,他们都能预测对方的反应和看法。
所以,有时候他们甚至不需要说话,因为彼此心里都已经知道对方会怎么说了。
比如在一些他们意见不同的事情上(特别是慈善事业),他们就倾向于保持沉默。政治观点也不完全一致,但他们从不争吵,只是各自为政。
他们依然是最亲密的朋友,只是这份友情已经到了只用心领神会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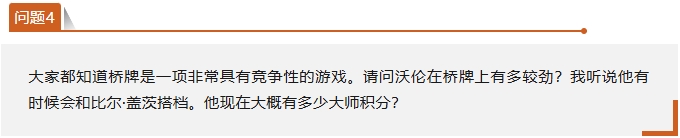
施罗德 沃伦的搭档是莎伦·奥斯伯格(Sharon Osberg),她是两届世界冠军。她把沃伦从一个业余爱好者训练成了职业玩家。
他曾参加过国家级的桥牌锦标赛。不过关于他的积分,我不太清楚系统,也不知道具体数字。
莎伦可能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在公开场合不常提这件事,因为可能会让其他自认是他最亲密朋友的人不太高兴。但事实上,是莎伦长期陪伴在他身边。
她也经常和比尔·盖茨搭档,而且现在越来越多地和比尔一起打比赛。
沃伦过去在桥牌上比比尔厉害一些,但随着比尔花更多时间练习,也正在追赶上来。至于积分的具体数字,我确实不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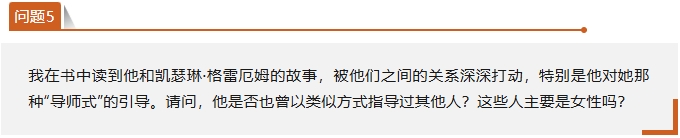
施罗德 他还指导过其他人吗?他们都是女性吗?可以说非常少。
我确实看到过两次,有人加入伯克希尔·哈撒韦之后,以为会受到他的亲自指导。他一开始确实会特别热情,也有点沉浸于那种感觉。
他会给这些人安排工作,花半小时和他们聊聊,然后……之后就基本不再见面了。
他不是那种“单对单”的教练型人物,他不喜欢那样。他喜欢站在一群人面前讲课,分享经验。
而跟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关系不同,那真的是他人生中唯一一次投入那么多时间、精力去指导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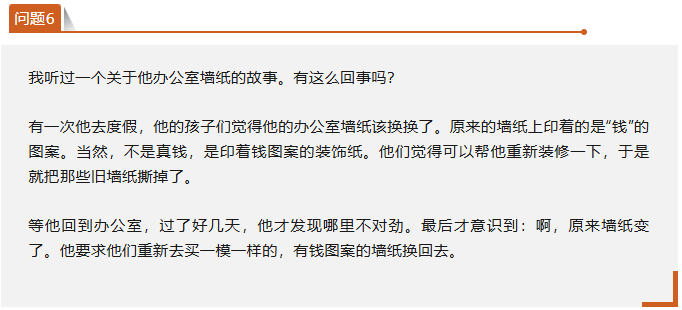
施罗德 这个故事是真的,确实如此。
他女儿经常帮他采购,比如帮他买车。
他非常讲究性价比,会要求她跑遍多达四十家经销商,去寻找同款中最便宜的那一辆,甚至可能是因为车被冰雹砸过更便宜。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朴谷咨询立场。